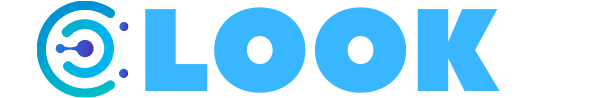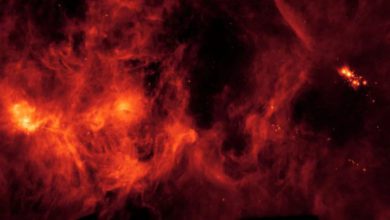大明天啟六年(1626年)五月初六日,這是一個與以往沒有什麼太大不同的日子。儘管從萬曆中期開始,大明朝就已經是危機四伏,邊疆多警、旱澇頻仍、流民遍地、烽煙四起······。但是,帝都依然繁華,在大多數士庶眼中,大明還是那麼厲害了的,誰又能想到這離亡國不過只有18年了。
在這個尋常的日子,大約上午辰時的時候,北京內城西南角的火藥工廠——王恭廠附近忽然從東北方傳來狂吼的聲音。隨即,大震一聲,頓時天崩地塌,屍橫遍地,場面恐怖至極。長安街一帶,人頭、殘腿、斷臂紛紛墜落,石駙馬街有5千斤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。
這場突如其來的天變也波及皇宮大內。因為出於武器控制的考慮,當初明成祖沒有把火藥工廠放在城外,而是放在城內的犄角旮旯的地方,王恭廠被認為是個安全的地方。哪裡想到,會出這麼一檔子恐怖詭異的事情。當時正在乾清宮的天啟皇帝也驚慌不已,隨侍的兩名太監則被震塌的殿瓦當場砸死。正在皇極殿上施工的兩千多工匠全部被震死,屍體堆在宮殿廣場。

王恭廠大爆炸
除此之外,不少京城官員也在這場天變中遇難,如工部尚書董可威失掉雙臂;御史何廷樞、潘雲翼被震死,全家覆入土中。相隔180里的薊州城也受震動,城樓東角及數百間房屋坍塌。更為詭異的是,無論死者、生者,都衣飾全無,而西山一帶樹梢則掛滿衣物,昌平州校場也堆滿衣服、器皿以及銀錢首飾之類的物品。
這場災難帶來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是巨大的,但是在當時官員隱匿之下,上報朝廷的損失數字被大大壓縮,他們匯報的是“塌毀房間共一萬零九百三十一間,壓死男婦五百三十七人。”這個數字與當時很多親歷者的記載並不一致,大宦官劉若愚在《明宮史》中說:“殺有姓名者幾千人,而闔戶死及不知姓名者,又不知幾千人也。”

天啟帝
高汝栻在《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》中所記傷亡數字則更令人瞠目結舌:“王恭廠之災也,······震倒民房一萬九百餘間,人民壓死者五萬七千餘人,被磚石伏掩者又不計其數。”據現在的明史學者依據史料,參照災變損毀的面積與人口、房屋的密度進行推算,也認為塌房萬餘間、死亡萬餘人的說法比較可信。
從成祖遷都北京之後,北京的地震其實並不算稀奇事,但是這次詭異的大災卻令人恐怖,波及範圍之廣,傷亡損失之慘烈,以及種種現象之怪異,人們聞所未聞,見所未見,故而也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恐慌。晚明筆記《梼杌閒評》中說,當時的京城“一城中驚得鬼哭神號······直至兩三日後方定。”

《梼杌閒評》
在相信天人感應的古代社會,在這樣災難面前,真正最慌的是朝廷,是皇帝。所以,朝廷除了撥款1萬兩白銀賑災之外,天啟皇帝朱由校還下了修省詔書,也就是自我反省書,號令大小官員共同修省,消餌天變。除了皇帝本人之外,當時權勢炙手可熱的魏忠賢閹黨也慌得一比,魏忠賢的親信司禮監秉筆太監李永貞可能是最慌的一個。
這一年的四月二十九日,李永貞在隨朝之時跌傷左腿,在梨園直房調治,這時可能就已感覺到冥冥之中自有天理,覺得自己在朝堂之上跌傷大腿實屬報應,而五月初六日王恭廠大災則讓他更為恐懼,請求退隱,雖然最終沒辭成職,但這種恐慌卻在閹黨內部蔓延。
很多在政治上原先屬於閹黨集團的官員,卻在此時以天變為契機,上疏要求朝廷整頓政治,這恐怕就是天變所致的政治恐慌。天啟皇帝發佈修省上諭的當日,大學士顧秉謙等人以“陰陽五行”、“天人感應”為理論,認為王恭廠之災系“陰奸陽”的表徵,而落實到人事上則是刑獄不清,怨抑過重,因此,“請敕在京各衙門重大獄情經奉明旨俱開選法司,分別具奏,速與發落,在外責成撫按、有司不許淫刑以逞,庶天心嘉悅矣”,並彈勃自己,請求罷斥。

魏忠賢
緊跟著的第二天,兵部尚書王永光上疏請求修省,認為王恭廠之災“必朝有紕政,位有奸人,顛倒悖謬’所致。更有甚者,五月二十九日,吏部尚書王紹徽的上疏則更為激烈,直接批評皇上不知輕重緩急,民命之所關,安危之所繫,舉措政綱皆本末倒置。並告誡皇帝,刑賞乃君主之權柄,不可濫興大獄,屈打成招,否則只會天怒人怨。這顯然不像一位臣子對君主說話的語氣,其間充斥著教訓和指責。
這些依附於魏忠賢的官員們,為什麼這一次有這麼大的膽子和勇氣,敢不顧政治前途,甚至有點不顧生命地上疏說真話呢?原因可能就在天變上,駭人恐怖的天變讓他們慌得一筆,末世的危機感激發了他們的政治良知,所以才會有這樣反常的政治舉動。可以說,日後崇禎執政之初,魏忠賢的倒台,王恭廠大爆炸其實是奠定了政治基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