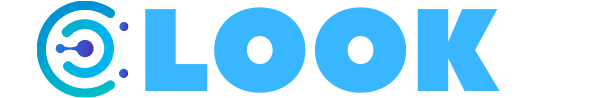在歐洲,匈牙利屬於存在感很低的國家之一,9.3萬平方公里面積約生活有970萬國民,人均GDP已多年緩降至1.8萬美元。但在19世紀,匈牙利與奧地利組成的奧匈帝國可沒少給歐洲各國找麻煩,雖然一戰後解體,但二戰剛爆發匈牙利又加入軸心國行列,哪怕二戰後的匈牙利也與其他歐洲國家有著明顯的差異。


在布達佩斯多瑙河游輪上,我的嚮導蒂姆·瑪麗告訴我:匈牙利人的外貌與其他歐洲人沒什麼差別,但內在文化卻存有諸多不同,比如匈牙利人的名字與中國人一樣,姓在前名在後;絕大多數歐洲國家的語言都出自印歐語系,而匈牙利語與芬蘭語、愛沙尼亞語卻是烏拉爾語系,歐洲各大語系因此將匈牙利人當成“歐洲的外來者”。
1950年,匈牙利爆出一個“寡婦村”的惡性案件後,使得歧視匈牙利人的行為傳遍整個歐洲,2005年還有人拍了一部名為《天使製造者》的紀錄片來警告人們:千萬不要娶匈牙利女人。


歐洲人所說的“匈牙利寡婦村”實際名為納吉列夫(Nagyrev),位於首都布達佩斯東南方向60公里處,這一帶土地肥沃且緊鄰多瑙河,是布達佩斯政府明令禁止工業汙染的農場集中區。然而,納吉列夫卻一副蕭條破敗如無人村一般,這一切皆因一名女助產士而起,她的名字叫蘇珊娜·法則卡斯(suzsanna·fazekas)。
瑪麗說:匈牙利人管她叫“毒藥攪拌機”,如果沒有她和她製造的毒藥,至少紀錄片不會那麼寫。

1911年,蘇珊娜與醫生丈夫投靠表兄搬家到納吉列夫生活,對於當時的匈牙利鄉村而言,多了兩個醫生和助產士村民,無疑是件值得慶幸的事。很快,蘇珊娜的丈夫靠著醫治村民們的頭疼腦熱等小毛病,很快就被村民們奉為上賓,而蘇珊娜則扮演了“知心姐姐”的角色,為村中女性解決一些男醫生不方便處理的問題。

夫妻倆很快就開了一家方圓十多個村莊唯一的診所,幾乎每天都有人趕來看病,使得夫妻二人的聲望越來越高,連帶蘇珊娜表兄也被推選為納吉列夫村的“保長”,專門負責村莊的治安以及突發事件。誰也沒想到的是,蘇珊娜的丈夫沒過多久就突然消失了,一開始蘇珊娜對村民說是出遠門問診,遲遲不歸後又說已經死了,在“保長”表兄的證明下,村民們也只能勸其節哀順變就散了。
而蘇珊娜並沒有離開這個“傷心之地”,反而聘請店員繼續經營診所,而醫治的對象卻從村民變成了只接待女性。

第二年,蘇珊娜在所有村民匪夷所思的目光中嫁給了村裡的另一個男子,更不可思議的是,第二任丈夫沒多久突然病逝了,由她的表兄為其開具死亡證明草草下葬。
就在這個時候(1914年),奧匈帝國聯合德國向塞爾維亞宣戰,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,納吉列夫村九成男性被徵調前線參加戰爭,上到55歲、下到16歲的成年男子一下全走空了。但村裡的女人們卻沒有那麼悲傷,反而有種解脫的慶幸,因為當時的匈牙利男子對待妻女經常大打出手,蘇珊娜的診所就是專門為這些被家暴的女子服務。

1915年,奧匈帝國把第一座戰俘營設在納吉列夫村田園處,因為這裡沒有樹林和遮擋物,更方便管理。對於丈夫離開一年多的納吉列夫婦女而言,這批戰俘的到來不僅增加了人氣,同時也使得“半守寡”的她們春心浮現,漸漸的,村裡大量年輕婦女與戰俘們有了不明不白的關係,甚至有人同時與多名戰俘保持交往。而戰俘們也樂的有她們相伴,閒暇時間就主動提出為她們分擔農活,一時之間其樂融融酷似合法夫妻。

而蘇珊娜此時的角色又從“知心姐姐”變成“解決問題的姐姐”,很多婦女懷孕後只能求助蘇珊娜為其打胎,這也進一步使蘇珊娜更受納吉列夫婦女的尊重,或者說是懼怕。
在之後的三四年裡,蘇珊娜至少有10次被逮捕,但一名支持墮胎的法官卻堅持將其無罪釋放,無數次的縱容再加上村民們的奉承,使得蘇珊娜名利雙收,甚至在布達佩斯買房用作與戰俘私會之所。

好景不常在,1920年匈牙利戰敗,七成土地被割讓,大量士兵被俘虐待數月才被釋放回家。可灰頭土臉的納吉列夫男子回到家後才得知,自己在前線拚死戰鬥,而妻子卻在家中與敵方戰俘有染。從此,納吉列夫男子對待妻子的態度更加惡劣,動輒打罵,家務農活也一概不理。

1920年夏天,村裡一名婦女帶著一身的傷找到蘇珊娜哭訴,而蘇珊娜一邊為其塗抹藥水一邊勸她“換一種生活,比如我這樣的”。
蘇珊娜的“換一種生活”就是毒死丈夫,她教給這個婦女一個方法,收集粘蠅紙中的液體,或乾脆把沾滿蒼蠅的粘蠅紙直接煮開,把水加入米飯或湯裡。而這個婦女照做一個月不到,她的丈夫就在深夜死去。在蘇珊娜表兄的“死亡證明”裡,死因被描繪成心臟病發。

很快,納吉列夫村和隔壁幾個村的男子陸續出現各種罕見病症相繼死亡,除了零星幾名男子癱瘓在床無法言語外,絕大多數死者都的死亡證明都寫著心臟病發,到後來,表兄覺得總是心臟病未免太過駭人,後半部分的死者就乾脆被寫成死因不明或罕見病症。
由於粘蠅紙的毒素需要長期服用方能致死,蘇珊娜後來給婦女們的大多數都是砷,也就是古代中國人說的砒霜,而多瑙河北岸就有一座紅信石主體的小山坡(含少量硫化砷)。

1929年,匈牙利警方接到一名醫生寄來的匿名信,信中寫到醫生是附近城鎮的居民,去納吉列夫參加親友葬禮時意外發現,死者嘴唇發黑且身上有不規則血斑,是明顯的中毒症狀,但當地卻出具了罕見病症的死亡原因。
聯想到納吉列夫和鄰村在過去十年中共有300多名男性死亡,醫生懷疑背後有黑手在操控,因此向警局發出提示。

當警察們趕來時,納吉列夫村婦女在蘇珊娜的帶領下,一面以“天使製造者”的名義阻止他們進村,另一面則抓緊轉移屍體。照片中的這名女孩在父親墳前告別,因為母親告訴她幾分鐘後就要挖出屍骨丟入多瑙河。
等警察突破阻攔進入村中時,仍有十多具屍體被挖出等待運往河邊,警察隨後趕往河邊,卻只攔下區區幾具。


為此,布達佩斯報紙以“多瑙河被拋屍百具”的標題公佈此案,實際上,報紙所說的並不準確,因為被拋棄的屍體有180多具。警察隨後將過去10年意外死亡的墳墓全部挖開,從而確認其中121具死於中毒,因此逮捕100多個寡婦,而其餘人則因為屍骨消失而躲過一劫。
布達佩斯老人都知道,納吉列夫村之所以沒有橋樑通往對岸村莊,是因為這個碼頭就是當年丟棄屍骨的地方,對岸村莊才極力反對修建橋樑連接納吉列夫村。


布達佩斯警方一共起訴了其中的34名婦女,其中26人是堅定的“天使製造者”成員,她們不僅毒殺自己的丈夫兒子,甚至還協助其他成員犯罪。然而,經過那名堅持墮胎的法官斡旋,最後雖8名婦女被判死刑,但真正執行死刑的只有兩人,蘇珊娜則以“病重”為由被輕判20年刑期。
匈牙利“集體毒夫案”和“寡婦村”的新聞隨後被歐洲各國瘋狂轉載,布達佩斯法官的判決更是被認為是“公開的縱容和包庇”,在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裡,斯洛伐克、塞爾維亞、奧地利以及羅馬尼亞等鄰國,紛紛勸誡國民“迎娶匈牙利女子需加倍小心”。


如今,納吉列夫仍然是匈牙利人乃至歐洲各國遊客都十分嫌棄的地方,哪怕10歲就從奶奶口中聽說此事的瑪麗,帶我進入村莊時也是一臉“不待見”的表情。
環顧了一遍納吉列夫村,幾乎家家戶戶都是門窗緊閉,只有村中心環島處有幾個遊客騎自行車路過時張望了一下。臨走時瑪麗說:你是我接待的第一個要求來納吉列夫村的遊客,希望沒有下一個。